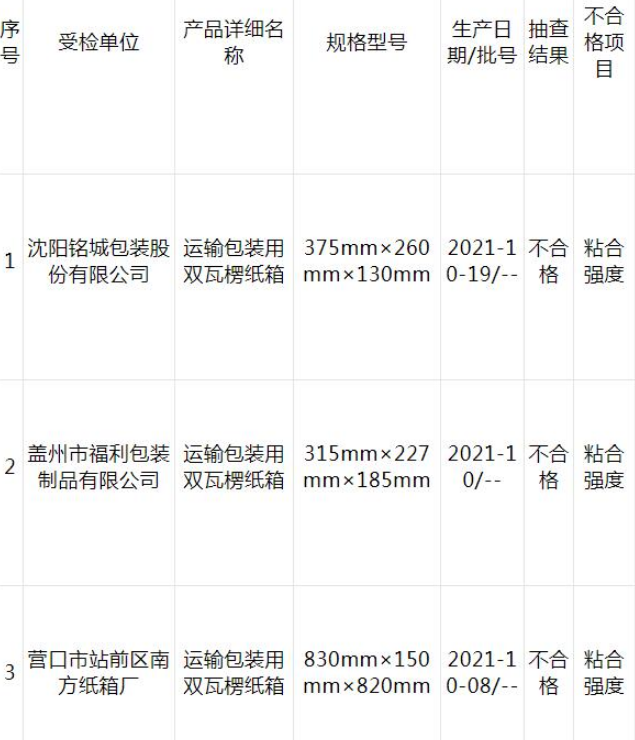时代的记忆与历史的乡愁:家是回忆的对象,也是回忆的载体
长篇小说《客乡》是德国作家燕妮·埃彭贝克的作品,入选莱比锡图书奖短名单(2008)和《卫报》21世纪百佳图书(2019)。本书名为“客乡”,实际上写的是发生在作者的祖国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一片湖边的故事。围绕湖边两处房产,作品在房子主人、访客和租客等的人生际遇中,隐喻了20世纪德国历史变幻的诡谲风云,在固定空间里完成了时代历史叙事。
 (资料图)
(资料图)
小说家燕妮·埃彭贝克
《客乡》 燕妮·埃彭贝克 著 李斯本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家的记忆
家是每个人都熟悉的概念。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一种自然存在,与生俱来、如影相随,不会唤起失去的担忧和刻意的珍惜。只有经历了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之苦的生灵,才能痛感家的可贵。
家是空间意义上的居所,更是情感意义的归宿。本雅明说,人类对居室的需求是永恒的。只有物理层面上安顿下来,人类才可以畅享“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很多家庭无法保留住自己的栖息之地,尤其犹太人,先是自由选择居住地这一最基本的人的权利被剥夺,后是集中营和毒气室的噩梦。《布料商》一章里那个犹太家庭即经历了这一历史磨难。生死转圜之际,一家人念念不忘的只有这个字:家。《作家》一章中,有一个犹太母亲的女作家流亡苏联之时,一边书写着“所有要将德国的野蛮人变回人类,将她的故乡变回故乡的文字”,一边念念不忘的,也是这个字:家。而在流亡、思乡过程中,女作家终于领悟到作为这个时代的个体的处境——“永生永世的无家可归,无论他们最后归来与否。”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家乡,也是客乡。
在不断被冲击和粉碎的犹太家庭里,关于家的记忆由一处处数不清的细节构筑。摧毁越无情,细节越清晰,记忆越完整。《布料商》一章里,主人公的外套、裙子、茶具、鞋子、铝制回形针、开信刀等,都被作者不厌其详地给出了购买时间和价格。这种看似琐碎的书写,突显出凡俗的日常生活对于当事者而言的珍贵和价值,也表达了作者用细节对抗忽视和遗忘的坚定态度。
《客乡》拒绝遗忘的,不仅仅是家的记忆。《女孩》一章中,犹太人被拍卖的各种家庭物品,童年的小床、壶、六角手风琴、床单被套等,作者明确了它们的去向——购买者都是一群有名有姓的普通人。在普通人参与的这个邪恶历史进程中,有谁是脱离罪恶的无辜者?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疑问,似乎弥漫在历史的各个角落。
低吟的哀伤
《客乡》中,家不仅是回忆的对象,也是回忆的载体。德国文化记忆研究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指出,如果不想让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在未来消失,就必须把它转化成后世的家庭记忆。为拒绝遗忘、长存记忆与人之情怀,重复是《客乡》采用的最重要的写作和修辞手法。事实的重复、细节的重复、情境的重复、关键词的重复,既营造出一种徘徊吟咏、意味悠长的抒情效果,也不断提示重要的事实或情感内核。
首先,重复被用来反复提示作者关心的重要情节。在只有短短二十页的《布料商》一章中,有一段内容出现了三次,在书写形式上如同诗歌一样被分成六行,只为介绍一家三代的名字、相互关系。这一家人,父母和妹妹全家都死于集中营,儿子一家因早早移民南非而幸免于难。这三次重复意在提示读者,一个普通犹太家庭承受了多么大的苦难和牺牲;同时也宣示,这个家族的血脉并没有断绝。这种延续既有在生物基因意义上血脉绵延,也在家庭文化记忆意义上永志不忘。幸存者用死去的妹妹的名字为自己的女儿命名,昭示的就是拒绝遗忘。在时代的黑夜中,除了隐忍和见证,以重复拒绝遗忘是普通人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无论对于作品中的人物,还是对于写作者本身。
其次,重复还能酝酿和深化情感。《作家》一章中,流亡女作家回忆和记录自己辗转柏林、布拉格、莫斯科、乌法,再经莫斯科重回柏林的过程,短句“我——要——回——家——了”被重复了五遍。虽然作为一代理想主义者,女作家要回的家,更像是“思想的家”,“一方不再是缥缈游魂的土地”,但流浪者回归家园的渴望,却在重复中不断被深化。
再次,重复是断续的碎片化回忆的复现。在《访客》一章中,来自波兰的老太太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最后,有一长段文字对此前回忆内容进行了选择性重复。这一段重复也像诗一样分行排列,涉及的内容有动作、有情绪,也有感觉,模拟的是老人模模糊糊、断断续续的思绪。
此外,从整体结构看,还有一种明显的形式上的重复。除去序言和尾声,全书形式上共二十二章。其中,同名的十一章《园丁》,均匀分布于其他十一章每章之前。不过,这些“园丁章”并不承担主体故事,每一个“园丁章”,都在讲述园丁的工作,四季的轮回。
通过重复,《客乡》成了一首抒情诗。在关于家庭记忆的叙事中,不同形式的重复此起彼伏、回环往复,产生了低吟的哀伤。这哀伤曲折深致,直抵人心,久久回环。
沉默的大地
《客乡》开篇即从地质运动角度介绍了勃兰登堡州这片湖泊的形成过程,借由自然史的尺度和视野,作者的眼光和叙述不但超越了当前、此地生存的人群的生死,甚至也超越了人在此地生息的历史,把人类的活动纳入了更深远的时空框架。
与这个时空框架相配合,作品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结构形式。十一章《园丁》,仿佛一个立体的多层搁物架,其他章的人物故事就在这自然“之架上”顺序摆列,条理分明,秩序井然。而十一个《园丁》章依次出现,除了也是作品的一种重复形式,更指向一种内在的坚实与恒定,构成了宛若一章的整体。在《园丁》各章中,重复的内容不仅是季节,还包括园丁的各种动作、土地的质地和颜色、植物的生长和培育。这些与大地紧密勾连的生活和事物,令人感觉人世固然纷扰变幻,仍有恒然不变者在。正如顾城在诗歌《墓床》里的感叹“人时已尽,人世很长”,在勃兰登堡州这片湖泊边,在生生不息的人间,坚不可摧的大地承载着一代代人在口头交流中形成的群体记忆,已经超越了时间和历史。大地沉默,并非无言。
《客乡》篇幅并不长,却涉及了很多20世纪德国社会的问题。譬如《建筑师的妻子》《红军军官》两章中谈到战争暴行,《访客》涉及国际移民,《转租人》讲述了两德分立时期的偷渡问题,《童年好友》暗示着城乡差距问题,《非法所有人》则是对两德重新统一后的历史问题的清算。在百年的家庭记忆和历史记忆中,《客乡》让我们看到:个体的生活在时代的大船上随波逐流,任由历史在漩涡中打转。在这个意义上,人间炊烟处处,总归皆是他乡。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伟东(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流程编辑:u008
版权声明:文本版权归京报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改编。
标签:
下一篇:最后一页
- 券商第一梯队海通证券遭遇多事之秋:业绩与规模“双降”
- 纸浆期货是否有效对冲废黄板纸现货价格波动风险?
- 理文、山鹰发布停机函 包装纸市场涨价100-200元/吨
- 全部合格!广东珠海抽查5批次油墨产品
- 浆系纸种再掀新一轮提价 涨幅达200-1500元/吨
- 保定满城区开展纸制品行业专项检查 规范纸制品企业生产
- 2022年3月14日全国各地区纸厂废纸价格信息
- 包装材料、人工费等成本上升 台湾生活用纸涨价
- 上周木浆系纸品价格均有提涨 箱板纸价小幅下跌
- 景兴纸业2021年营收同比增27.70% 净利同比增41.51%
- 1-2月全国快递业务收入1574.3亿 同比增长13.8%
- 原料成本压力持续上升 浙江多家包装厂产品价格上涨3%
- 3月7日-13日生活用纸主要区域市场周度价格情况
- 安徽出台“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规划
- 原材料/燃料价格上涨 日本卫生纸、纸尿裤提价超10%
- 新加坡超市将对塑料袋收费 至少5分新币/个
- 电子商务兴起 印度纸类包装行业发展趋势
- 2022年1-2月芬兰木材交易同比下滑20%
- 山东造纸行业深入实施“链长制”工作推进机制
- 包装原料价格波动再成热点 揭秘2021造纸上市企业业绩
- 国家统计局:1-2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7.5%
- 2022年3月18日各地区各大纸厂废纸价格信息
- 江苏开展精准造林绿化 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和全民义务植树
- 正隆纸业员工返岗率超95% 预计今年营收同比增10%
- 芬林芬宝劳马新锯材厂将启用自动装载生产线
- 山东一小镇发展纸箱包装生产企业近百家 年产值11亿元
- 打破性别“玻璃天花板” 95岁女院士是“她力量”最佳代言
- 河北辛集市暂停举办体育活动 关闭景区文娱场所
- 红色文物·党史故事 “推出胜利”的小推车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闭馆
- 核酸采样:一位“点长”的50小时冲刺
- 跑道结冰 哈尔滨机场关闭至9日12时
- 北京地铁全面开启车内加热装置
- 黑河市多举措保障疫情期间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生活稳定
- 北京丰台海淀两处管控区域解封 社区工作者收到“暖心礼物”
- 吉林四平一旅游项目违占耕地两千多亩 投资达10亿元
- 湖南双峰27名非法滞留缅北人员被惩戒:小孩回原籍入学
- 江西新增本土“1+6” 上饶增一中风险地区
- 江西上饶一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实行封闭管理措施
- 快递旺季遭遇雨雪天气 国家邮政局呼吁理解快递小哥
- 高压、孤独,胆大、心细:手执焊枪的水下“蛙人”
- 掏粪掏了36年,他还在琢磨“新门道”
- 内蒙古:二连浩特市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额济纳旗累计治愈出院本土确诊病例76例
- 坚守在海拔4300多米的“天路保健医生”
- 38年后,他终于知道了家在哪儿……
- 受降雪影响 辽宁鞍山一农贸市场发生坍塌
- 中国舞蹈家协会顶尖教师巡回课堂(重庆站)举办
- 边城战“疫”:夜晚七点的暂停键
- 风雪高原战“疫”长卷 寒潮下的西宁疫情防控观察
- 拟音师:“雕刻”声音的人【三百六十行】
-
“双减”之后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为何依然火爆
聚焦 “双减”之后,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为何依然火爆 近日,2021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
大数据助力贫困生成长
探索 大数据助力贫困生成长大数据画像能为贫困生成长带来什么 今年9月,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
“大漠明珠”驶上发展快车道 塔里木盆地做足生态大文章
塔里木盆地做足生态大文章 “大漠明珠”驶上发展快车道 从塔里木盆地的西北角到西南角,和田...
-
职校生可报考事业单位 搬走职业教育的一块绊脚石
职校生可报考事业单位 搬走职业教育的一块绊脚石 “职业院校毕业生也可以报考事业单位了。”...
-
打算“双十一”买买买的姐妹 看完这篇再“剁手”
打算“双十一”买买买的姐妹 看完这篇再“剁手” 女性对于保养的热衷超乎想象,不少人只要是听...
-
完美“飞天”仰仗全宇宙最酷飞船试驾员
完美“飞天”仰仗全宇宙最酷飞船试驾员 11月7日,航天员翟志刚、航天员王亚平开展神舟十三号航天...
-
冠状病毒中损伤血管的蛋白首次确定
冠状病毒中损伤血管的蛋白首次确定 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刘霞)不少...
-
新电池结构让飞行汽车成为可能 相关技术将亮相北京冬奥
新电池结构让飞行汽车成为可能 相关技术将亮相北京冬奥会 科技冬奥进行时 搭载全气候电池...
-
H5N8病毒肆虐全球,我国家禽为何“独善其身”
H5N8病毒肆虐全球,我国家禽为何“独善其身” 科技日报哈尔滨11月7日电 (记者李丽云)记者11月7...
-
重庆奉节一民警因公殉职 年仅28岁
中新网重庆11月9日电 (记者 刘相琳)记者9日从重庆市公安局获悉,重庆奉节县公安局民警袁华押解一...
-
哈尔滨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
中新网哈尔滨11月9日电 (记者 刘锡菊)9日,哈尔滨市卫健委发布哈尔滨市11月8日0-24时疫情通报:11...
-
成都本地累计在管密接2757人、次密9097人
(抗击新冠肺炎)成都本地累计在管密接2757人、次密9097人 中新网成都11月9日电 (记者 贺劭清 ...
-
成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例 出现1传13特殊案例
(抗击新冠肺炎)成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例 出现1传13特殊案例 中新社成都11月9日电 (记者 贺劭...
-
呼和浩特一学校宿管员扇打学生致双耳鼓膜穿孔 分管校长被免
中新网呼和浩特11月9日电 (记者 张林虎)9日,针对“宿管员扇打学生致其双耳鼓膜穿孔”一事,呼和...
-
郑州通报8例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
中新网11月9日电 据郑州市委宣传部官方微信消息,11月8日0至24时,郑州市新增阳性感染者3例,均为...
-
新疆阿克苏果农:我们的生活像苹果一样甜
中新社新疆阿克苏11月9日电 题:新疆阿克苏果农:我们的生活像苹果一样甜 作者 苟继鹏 “我...
-
河北辛集开展大规模消毒消杀工作
今天(9日)上午,河北省辛集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辛集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辛彦卜介绍,新冠...
-
河北辛集新增本土确诊11例 已转运定点医院诊治
今天(9日)上午,河北省辛集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辛集市副市长刘士民介绍,2021年11月8日0时至...
-
石家庄深泽县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11月9日,石家庄市召开第12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石家庄市深泽县县长郝英鹏...
-
海口市1例治愈后的境外输入病例复阳 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医学观察
中新网海口11月8日电 (记者 张茜翼)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8日通报称,11...
-
四川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例
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四川省卫健委网站消息,11月7日0-24时,四川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5例(...
-
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6例
中新网哈尔滨11月8日电 (程岩 记者 史轶夫)黑龙江省卫健委8日发布消息,7日0-24时,黑龙江省黑河...
-
河南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例 其中郑州市16例周口市2例
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河南省卫健委官方微博消息,11月7日0—24时,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例(郑州...
-
河北新增确诊病例8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
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河北省卫健委网站消息,2021年11月7日0—24时,河北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
寒潮持续发威!南方气温纷纷触底 强降雪中心转移至东北
中国天气网讯 今天(11月8日),寒潮继续南下,持续发威,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纷纷触底。强降雪中心将...
-
雪后寒!今日北京晴天回归北风劲吹 最高气温5℃上下
中国天气网讯 今天(11月8日)北京晴天回归,但在风寒效应下,“冷”仍然是天气的主题。气温方面,今...
-
黑龙江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例 均在黑河市爱辉区
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黑龙江省卫健委网站消息,2021年11月7日0-24时,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
-
寒潮继续影响华东华南等地 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雪
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受寒潮影响,预计11月8日08时至9日08时,黄淮东部、江淮东...
-
辽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0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2例
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辽宁省卫健委网站消息,11月7日0时至24时,辽宁省新增20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

寒潮影响“加码”:吉林力保电力供应 停课停运范围加大
中新网长春11月9日电 (记者 郭佳 张瑶)连日来,一轮寒潮引发的强降雪席卷中国北方。位于东北地区...
-
常州连续一周无新增病例 10日全市各类学校将错峰复学
中新网常州11月9日电 (记者 唐娟)11月9日,常州疫情防控指挥部学校防控组对外发布,自11月10起,...
-

哈尔滨机场开放恢复运行 计划航班45架次
中新网哈尔滨11月9日电 (仇建 记者 史轶夫)9日12时22分,随着哈尔滨经阜阳飞往三亚的FU6685航班...
-

山西警方抓获6名“摸金校尉” 缴获“虎枕”等大量文物
中新网长治11月9日电 (记者 李庭耀)记者9日从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上党分局获悉,上党警方侦破系列...
-
西藏基层第一书记话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
中新网日喀则11月9日电(记者 赵朗)近日,由西藏自治区网信办主办的第一书记话小康活动先后走进山南...
-

内蒙古通辽:强降雪致8个旗县区受灾
中新网通辽11月9日电 (记者 张林虎)9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应急管理局获悉,自11月5日起,...
-
成都金堂:医护人取消婚礼坚守岗位 手捧花被送到了战“疫”一线
中新网成都11月9日电 (邹立杨)连日来,华西医院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实验医学科的主检验师易维佳都在...
-
江西铅山新一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抗击新冠肺炎)江西铅山新一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中新网南昌11月9日电 (记者 吴鹏泉)江西省...
-
辽宁大连幼儿园和中小学学生即日起暂缓入校
中新网11月9日电 据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消息,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
-

2021年北京市重点碳排放单位:涉及多家印刷包装企业
3月15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了《关于公布2021年度北京市重点碳排放单位 及一般报告单...
-
北京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北京卫健委官方微博消息,11月7日0时至24时,北京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
-
河北石家庄深泽县7日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为8岁男童
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石家庄卫健委官方微信消息,石家庄深泽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8...
-
高速封闭、机场关闭、学校停课 辽宁多部门发应急预案应对极端天气
中新网沈阳11月8日电 (李晛 王景巍)7日在寒潮影响下,东北地区局地降大雪。辽宁省气象部门当日连...
-
云南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
中新网11月8日电 据云南省卫健委网站消息,11月7日0—24时,云南省新增确诊病例9例,其中境外输入...
-
努力让每个人都有出彩机会
努力让每个人都有出彩机会 “孩子明年要参加中考,成绩一直提不上去,送他读职高,也是一种选择...
-
参与和见证中国水电发展
参与和见证中国水电发展 余吉安的童年是在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岛的沙捞越州古晋市度过的。家门口的...
-
中国航天: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
中国航天: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科技名家笔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航...
-
8日起 江西铅山县开展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记者从江西省铅山县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为了充分保障公众的健康安全,现定于1...
-
适当“早教”可以,“早早教”大可不必
一家之言 适当“早教”可以,“早早教”大可不必 以前国庆节是放假了,可家家都有娃,放假补...
X 关闭
X 关闭